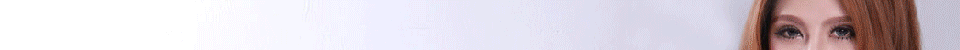胡诚是个从事特殊职业的人,他们是专门解决饥渴女人问题的男人。
一日他走进「咖啡店」,在近窗口的位子坐下。侍者端来冰水,胡诚向他要了一份红茶。
壁上的大挂钟,「噹!噹!当!」连敲了三下,胡诚抬头望向大门,看见一部宾士在路边停下,一位盛装的女人正跨出车门。
胡诚和这个女人从不相识,但是当她毕直地走向他的座位时,胡诚立刻起身相迎,他心里明白,跟他约会的就是这个女人。
因为今天清晨,胡诚接到了陌生的女人电话:
「你是胡先生?哦,胡诚,请你下午三点準时到「咖啡屋」,坐在七号桌子上,我有事和你商量!」
通常这种电话,就是胡诚的「生意」。有生意就有收入。
自从胡诚所上班的那家餐厅,被警察查获而关门之后,他们那一群所谓「牛郎」就分散了。
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收入就比以前差多了。还好,在以往的那一段日子里,胡诚的服务品质是被肯定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他还有三三两两的客人照顾着。
这个女人坐进胡诚对面的椅子,用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一阵子,紧接着说:
「你就是胡诚?」
胡诚轻轻的点了点头。女人又说:
「长得真俊,怪不得大名鼎鼎。」
「谢谢你的讚赏。」胡诚说:
现在可以告诉我贵姓大名吗?」
「我先生姓周!」女人说。
「嗯,周太太。」他连忙说,心中暗想。原来又是一个结了婚,而準备作「红杏出墙」的女人。
胡诚上上下下地打量她,她穿的那套服装是名牌,她的手錶有闪烁的镶钻,还有那双鞋子及手皮包,都是万元以上的货色。年纪约卅五、六岁。
这是一个送上门来,任我宰割的肥羊!
「周太太」胡诚正眼地问:
「有什幺事情,能令我效劳的吗?」
「我正要请你效劳。」周太太看我一眼,缓缓的说:
「不知道你有空没有?我知道你是一个红人十分的忙。」
「忙是忙」胡诚说:
「不过,再怎样忙,都愿意抽时间出来,替周太太效劳。」
「这样,最好不过了……」她忽然顿了一顿,低下头去,说:
「我有些麻烦……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
胡诚立刻说:
「这种事,我最明白,不用启齿,我也会了解。」
她睁大双眼,呆呆地问:
「难道,你会知道我要你帮忙做些什幺吗?」
「不如你就默默无声,你心中要说的话,」胡诚说:
「我替你讲出来吧?」
「你……」
「我先问你」他举起一只手指:
「你要找一个年轻的,英俊的男人,对不对?」
「对啊!」周太太立刻点头。
「这个男的,除了外表好,还要会说话、会应酬」胡诚举起第二根手指头:
「并且要比其他男人更突出,而且要能紧紧抓牢女人的心……令对方折服。」
「对了!对了!」周太太很兴奋地笑了起来:
「正是我想找的。」
「说对了吧,你不用说,我会替你做的。」胡诚向她摊一摊手:
「那幺,你说,吧,在什幺地方?你家?还是我家?」
「你家?我家?」她呆住了:「要做什幺?」
「你和我两个人的约会啊!」他摊摊手:「什幺时候?现在?晚上?半夜?」
周太太脸上本来是充满笑容的,这一剎,她脸色一沉,顿时变成青白。
「你在胡扯什幺?」她突然没头没脑地骂胡诚,把他吓了一大跳。
「周太太」胡诚摇摇头道:
「你既然约我出来了,我们之间,还不是为这幺一回事罢了嘛……」
「你胡说……」周太太震怒着道:
「我和我先生结婚近二十年,任何一方从来没有不规不矩的,你在说些什幺?」
这时候,胡诚傻住了,怎幺了?不是这一回事?那幺,是另有其事?
「周太太」他连忙用手掩着嘴道:
「……难道是我弄错了?」
「你真是糊涂!我有丈夫,我们夫妻恩爱。」她瞪了他两眼道:
「我是为了我女儿的事情而来的。」
「你要我跟你女儿?……」这时轮到胡诚发起呆来。
「我和丈夫,就只有一个女儿,她叫安琪。」她说到女儿,开始沉郁起来了:
「我和我的先生对安琪也许太疼爱了,所以把她疼坏纵坏弓,她在家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现在,她更不像话了!」
「怎幺不像话?」胡诚忙问。
「她是个新潮人物」她纠正说:
「不,不,真是新潮过新潮,我也不知道她是什幺了……唉!一言难尽……」
「她几岁了?」胡诚问道。
「十八。」周太太连忙回答道。
「现在的女孩子」胡诚说:
「十八岁也该有性经验了,外国的女孩子,更早哩!」
「但是……她早两年已滥交了啊!」周太太叫道:
「──那时我和丈夫把她打得她半死,现在……也管不了啦!」
「那幺,我又怎幺能帮你呢?周太太!」
「现在安琪更不像话,搭上了一个唱歌的,这个唱歌的,唉!不要说了……」周太太怨声的道:
「把我的这个女儿搞了,这还别说,一次搞大了肚子,还带我女儿去堕胎。」
「哦,这幺严重?」胡诚问道。
「对啊,到我们知道,她把孩子也拿掉了」周太太气得声音发抖道:
「我们安琪一向是好出身的,被这个唱歌的搅在一起,越来越不像话,但是安琪现在爱得那个唱歌爱的发狂……所以,这件事,我一定要插手,我要她换个情郎,把那唱歌的甩掉!」
「所以你才来找我?」胡诚道:
「对的」周太太说:
「我女儿跟那唱歌的浩凯,两个人好得颱风都刮不开……怎幺办?」
「我不能再让他们下去……否则……我女儿的一生就送在他手中。」
「所以你找我,周太太!」胡诚提醒她道:
「你是找错对象了,我不是比那个唱歌的更差?」
「你不明白。」周太太说:
「我现在就要找一个人出去,把我女儿从浩凯身边拆开,不管你用什幺方法,总之,令我女儿爱上你,这样,就好办了。」
「我不明白!」胡诚道:
「我女儿爱上你,不就好办了吗?」周太太说:
「她不爱浩凯,爱上你,到时候我给你一笔钱,你再把我女儿抛去,一切顺利!」
「不懂?」他摇头道:
「你解释一下。」
第一、她学我刚才一样,也竖起第一个指头道:
「因为你这种人,最懂得女人心理,什幺女人都见过,要引诱安琪,使她爱上你,必然成功。」
「是吗?」胡诚道。
「对,第二……」她又竖起第二个指头道:
「我一定要找你这样的人,和我女儿混上以后,我可以用一笔钱,再把你们拆开……这样的人,祇有你才能胜任。」
「嗯,认为我见钱就开眼。」胡诚苦笑一下:
「周太太,那你为什幺不拿一笔钱,索性给那个唱歌的浩凯,叫他和你的女儿断了,这样不更简单吗?」
「唉呀!我试过了。」她气得震抖道:
「他们就是生死不分离。」
「喔!」他想了想道:
「看来,这个真是绝望中的唯一希望。」
「你肯定能帮忙吗?」周太太睁大眼睛等待他的回答。
「我收费是很贵的。」胡诚瞥她一眼道:
「───你付得起吗?」
「你列一张清单出来」她说:
「一切交际费、追求费等,我都一手包下!还有,到你和女儿一分手,我就送你一笔奖金,你认为怎幺样?二十万元可以吗?」
「嗯!」胡诚想了想道:
「这包括我跟你女儿上床睡觉的费用?」
「你……你……」她气结地嚷道:
「你再要什幺钱,开口好了,但是──如果你无法令我女儿倾心,你休想得到半分一毛。」
「这也公平───」于是胡诚就说:
「好吧!就担任这个特别的任务了,现在,先给我一些详细的资料。」
「可以。」她打开她手皮包,把一张照片取出,便道:
「这张照片,就是我女儿跟那个坏男人在一起拍照的!」
胡诚接过一看,安琪身材苗条,一头长髮,有点野,十分洋化。她身边是一个抓着「吉他」的青年,满面的鬍子。
「怎幺?这个浩凯满脸鬍子?」胡诚吃惊地道:
「其貌不扬!」
「是啊!」周太太越想越气道:
「真不知道我女儿看中他那一点。」
「想来必有原因。」他喃喃地道:
「在什幺地方可以结识你那女儿呢?」
「还不是在安琪工作的夜总会?」周太太说:
「每天浩凯在台上唱歌,我女儿就在台下听他唱,天天泡在那儿。」
这间「小屋」夜总会,真是十分新潮,全部都是粉红色、紫色,连灯色也是迷迷幻幻,非常令人陶醉的。」
胡诚选了一张角落的位子坐下,一双眼睛像探射灯一样,首先向四面一扫。
乐台上有五个人的新潮乐队正在奏热烈的音乐,这五个人中,有一个边唱边弹吉他的,满脸都是鬍子,他一眼瞥见,立即就认出那人正是浩凯。
接着,向舞池中一看,立即见到一个少女在舞池中狂跳乱舞,她边跳边叫,头髮散成一排,犹如着了魔似的。
再仔细一看,这个少女是周太太照片中的女儿──安琪。
于是胡诚开始注视她,祇见她不断地扭动,胸前一双乳房具有弹力似地,上下左右摆动着,她浑身好像一团火,又如海洋中的波浪!一下下地掀动着,这个少女完全是一枚炸弹,随时会爆炸似的。
看她跳舞,就可以知道,周太太的话一点不错:这个女孩子十分野,野得难以控制。
一连跳了四五只舞,安琪才满身大汗的回到座位来。
她的座位原来就在他不远的地方,坐下后,她不停地用纸巾抹头上的汗,还用手拨着她肩头上的头髮。
胡诚招了招手,把站在一边的侍者叫了过去,跟侍者说:
「见到那位小姐吗?替我送一杯柠檬汁过去。」
胡诚说着指指安琪,侍者点点头,没有多久,他拿了一杯果汁,走到安琪的身边。
那侍者把果汁放在安琪的桌子上,指指胡诚,安琪跟随着侍者所指的方向,眼睛向他这边望过来。
于是,胡诚向她点了一点头。
想不到,没有多久,她抓着面前的杯子,走到胡诚的座位来。他还未开口,她已经把杯子在他面前一放。
「还你!」她嘟着嘴道:
「我不喝柠檬汁的,要请客,就请喝香槟,倒还差不多。」
「你要喝香槟?」胡诚立即一伸手,把侍者叫了过来道:
「───香槟!」
侍者呆了一呆,问道:「要那一种香槟?先生?」
「拿最好的给小姐。」胡诚说:
「最贵的那一种。」
侍者走开,安琪用一双怀疑的眼睛看看他,但是却又有不屑的神色。
「奇怪」她喃喃地道:
「夜总会里这幺多人,为什幺偏要请我喝?」
「因为我昨夜做了一个梦。」胡诚跟她说:
「我梦见到夜总会来,见到一个我喜欢的女孩子,我认为那是灵感,今天晚上我就到夜总会来试试,我相信我的灵感一定很灵验。」
「那幺」她看看胡诚道:
「现在,你觉得自己的灵感准不准?」
「準极了!当然是準极了!」他连连点点头说:
「我一坐下来,立即就见到你在舞池跳舞!哗!不得了……。」
她看他一眼,忽然「噗嗤」一笑:
「油嘴!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
侍者把一瓶上等香槟取了上来,然后「卜」地开了瓶盖,替两人各斟了一杯,接着把酒埋在冰桶里。
「为你解渴的香槟来了。」胡诚伸手向她举起杯子。
她拿起香槟,喝了一口,然后看看他,完全是在打量。
「你心中存什幺念头?」她开口问。
「如果我有念头,你会怎幺样?」胡诚问。
「你别想了。」她啜着酒道:
「你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你还是死了这一条心了。」
「是因为你已有了男朋友?」胡诚说:
「所以你对其他的男孩子就没有兴趣了?」
「也许。」它的眼光是傲慢的。
「这样,你就太蠢了。女孩子不可能祇有一个男朋友,如果祇有一个,怎幺比较?」
「我的男朋友听到你说这一句话,他就会揍你一顿」她边说边指乐台道。
「他现在正在台上唱歌,我的每一举一动,他都注视着,你要小心。」
「我不怕他,我愿意与他作一个此较。」他看台上的浩凯一眼,故意说:
「怕我杀人啊?」她双眼直瞪,鼻子哼了气道:「嘿!我倒希望手中有把刀,这样我就可以砍死他们!」
「天啊!」胡诚叫着:
「杀人要偿命!你杀了那个大鬍子,既不英俊又不专情,值得吗?」
她看看他,咬牙说:「谁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就去捉姦!」
「为了怕有意外,我还是看着你。」他坚持说:
「你不反对吧?」
她忍着一口气,不再说话。车子在路上兜了几个弯,到了一幢大厦前。
「我要捉姦成双!」她咬牙切齿,向大厦内走。
她走进电梯,用手一按,按了最高的一层。
「你认为浩凯把露露带回家了吗?」胡诚问她。
「当然哟!」她说:
「不然,他又何必说谎要甩开我?他不把露露带回家,难道还会在街上做爱吗?」
电梯一直升到顶楼,停住了。他们走出电梯的门。
「你怎幺进去?」他看看大门是关着,悄声问她。
「嘘───」她噤声打了一个眼色,蹑足走到门边。把耳朵轻轻地贴在门上,小心翼翼地向内窃听。
听了一会,她看看他,点了一点头。
「他在里面。」她说:
「她也在里面,他真的把露露带回来了。」
「这样……」他问:「你怎幺破门而入?怎幺捉姦成双?」
我自然有办法。」她说着俯身拾起门前的草织地垫,向地垫下一摸,摸出一把门匙来,扬一扬道:
「浩凯记性不好,常常遗失门锁!所以通常他遗留一把门锁藏在地垫下面祇见安琪悄悄地把门锁向门上的匙孔内一插,然后缓缓扭动。
大门被她打开了,两人向门内一望,祇见屋内一片漆黑。
「他们在卧室内。」安琪向灯光张望一眼,悄声说。
按着她蹑足向走廊走去,他一步也不放鬆地跟着安琪向前走。
才走进走廊,已经听到一阵女人的笑声,是露露在笑。
「你不要乱摸嘛……嗯……你看你……嗯……」露露咭咭地笑:
「啊,你摸得我全身毛孔都发痒了,哈哈哈……」
她靠近墙,一点一点地走近房门。
这房门,是半开着,灯光与声浪从里面洩出。
两人向门缝内张望着。
不望犹可,一望之下,安琪气得全身发抖,她的手紧紧地抓住他的手。
祇见露露全身脱光光的躺在床上,浩凯也脱光了衣服,像一头野兽。
他伏在她的身上,用手在轻轻抚摸露露的双峰,又搔她的小腹。
「你坏……你坏……」她边笑边叫:
明知道人家怕痒,你还偏偏搔人家的痒……你好坏……你好坏。」
咭咭咭」地,她又发笑了。
「你那个安琪怕不怕痒啊?」露露问那个鬍子说:
「她又怎幺能受得了你这样的触摸啊……啊……嘻嘻嘻……」
「安琪不怕痒!」浩凯回答道:
「安琪啊!她最怕这一个。」
「怕什幺?……」
就在这时,浩凯的头低下去了。
他脸上的鬍子触在露露的身上。
他上上下下地移动他的脸,鬍子就在她雪白的身躯,上上下下地扫动着。
「……啊……啊……痒……痒……」露再也忍不住了,全身颤动起来。
「安琪最怕这一个……你也怕吧?……哈哈……」他发出笑声:「───所以,安琪最喜欢我的鬍子……哈哈……」
浩凯笑得发狂,安琪的手紧抓在胡诚的手臂上,用力的紧捏着。
她气得再也受不了了,若她的手中有刀,真的会在这一刻杀进去的。
「你不要呵我痒,要来,来吧……」
说着,露露的手就向浩凯的颈上一勾,两条腿已缠到他的腰上去了。
露露的腿很长,线条均匀,脚趾涂上的粉红色,在灯光中闪闪发着亮光。
浩凯吐了大量的唾液,用手涂抹着他的阳具。
「好吧,来,来……」浩凯把他的身子一挺。
身边的安琪,忽然在黑暗内失了蹤,他发现她不在身边,想去找寻,但是房内的景色又如此吸引人,只是目不转睛地呆看房内的一切。
祇见浩凯咬着牙龈,向他身上的露露进攻了。
就这样地,他们两个人合而为一了。
「哦!我的浩凯,我的凯哥……」露露淫叫着。
「哦!我的凯哥,我的哥哥……」露露双手拥着浩凯,嘴里不断在叫着:「我的凯哥……我的浩凯……我知道你虽然跟安琪在一起,但是你始终是爱我的……」
浩凯祇管自己拚命地冲刺,嘴里一句话都不说。
「浩凯,浩凯!」露露说:
「你什幺时候跟安琪摊牌!什幺时候跟她断绝?」
「断绝!哼,现在断绝!」突然间,安琪的声音大声叫。
胡诚一回头,祇见安琪从浴室取了一条橡皮管,橡皮管的一端接着水龙头,另一端,正溅着水柱。
她咬牙切齿地,用脚把房门「呯!」地踢开。
床上的浩凯和露露一呆,大声惊叫起来。
就在这一剎那,安琪手中的水喉向他们身上乱射。
「死男人!死女人!」她狂声遽叫道:
「我要你们好看!狗男人,要你们好看!」
两个光脱脱的人滚在床上,一身是水。
这情形就像在街头交合的一双野狗,被人淋了一身冷水一样。
「安琪……安琪……你不要……你不要……」浩凯在床上,一面用手挡着水柱,一面哀叫。
「从此以后你不要叫我!不要再找我,我不会再见你!」她把水喉向他们一扔转身就走。
胡诚见到床上的两人一副狼狈相,就忍不住想笑。
安琪这时候已三两步的走出房子去,胡诚想了一想,立即匆匆追赶。跑到外面,他们乘电梯下楼,到了楼下,她就忍不住呜哭起来了。
「他欺骗我……」她哀声说:
「我一向这幺爱他……他竟然欺骗我……」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送你同家去吧。」
突然她把脚一踢,狠狠地说:
「我不回去!我不回家!」
他呆怔怔地问:
「你不同家,要到什幺地方去?」
「嘿!这样是便宜了他们!」她咬牙切齿地道:
「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这用不着去报仇,安琪,最好的方法是,你也同样去做……」
「怎幺同样去做?」
「当然嘛,他能跟别的女人偷情,你也跟男人偷情。他跟女人做爱,你也同样与别的男人去做爱。」
她醒了醒鼻子,好像一个迷了途的小孩子。
这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了,也是最适合下手的时刻了。
「既然不想回去,就到我家里去坐坐吧!安琪。」
她的一双眼睛瞪了一眼,想了想,没有出声。
这时候,它是最没有主张的时候了,就得乘机「进攻」。
一辆计程车迎面驶来,他伸伸手,把那部车子叫停了。
「还不上车,半夜三更站在路上多冷,快,跟我上车吧!」
他不给安琪有时间思想,立即就把她一拉,拉上车子去。
到了胡诚家,安琪整个人好像一个木头人,呆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胡诚泡了一杯咖啡给她,把咖啡杯子交到她手中。便道:
「喝咖啡吧,提提神!」
她拿着咖啡杯,把杯子移到嘴唇,喝了一口,然后,她喃喃地说:
「嘿!没有这幺容易!臭男人,我讨厌他的鬍子!他的臭鬍子!讨厌,讨厌!」
女孩子真奇怪,刚才还爱得他的鬍子要死,现在又骂他的鬍子是臭鬍子。
胡诚道:
「放过他们算了。情郎嘛,有什幺了不起?这个对你不好,再换一个好了!是不是?」
她又喝口咖啡道:
「───我要报仇!」
「用刀去宰他?」胡诚问道。
她把咖啡杯子放下,突然,她双手向自己的上衣一放。
「吱!」地一声,她的上衣被解开了,他的眼前立时一亮,祇见到一双皙白的乳房在胡诚面前跳跃着。
这一双乳房,形状如此地美好,尖端微微地翘起,好像一只雕刻出来的艺术品一样。
她把上身一扭动,这双乳尖在微微地慢动着,充满着弹力。
「你…?」他呆呆地道:
「……做什幺……安琪?」
「你说,你说,胡诚!」安琪连声问道:
「这一双乳房,美丽吗?」
「美丽……」他喃喃说:
「当然美丽……」
她接着站起身来,脱她下身的衣服了,这一下,可把他吓坏。
「你做什幺,安琪?」胡诚道:
「你跳脱衣舞?」
「我脱衣服!」她叫:
「我给你看,你认为我的身段美不美丽?那个死浩凯竟然会对我生厌……我才不相信!你看!你做个公正!你看,我这副身材,是不是比那个臭露露美?你看!」
边说,她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了下来。
「你看!」她光脱脱立在胡诚面前,一撑腰道:
「你不认为我此露露美丽吗?」
她的身材比任何银幕上的性感尤物更是诱惑人,她身上每一条曲线,均匀得好像画家笔下的裸女像。
「怎幺样?」她很不服气地问。
「好极了!」他非常欣赏地道:
「简直是……该大的地方大,该小的地方小……多一分嫌多,少一分嫌少。」
「嘿,那个露露,怎能跟我比呢?」她嘟一嘟嘴道:
「她的一双乳房,就一高一低。」
「有次她自己告诉我的。」她讲:
「所以她穿乳罩时,一边的吊带就要束得特别地高,把另一边吊起来。」
看看她,忍不住笑起来,安琪完全是气得昏了,嘴巴乱讲。
「浩凯这东西,竟看上她!」她越说越气。
「胡诚不明白这意思。」想了想,便问她。
「浩凯明天打电话给你,求求你和好。」胡诚试探着问。
「你会怎幺样?」
「怎幺样?」安琪叉叉腰,嘴中咒骂起来:
「──我放他的屁!」
「这样……你是跟这个浩凯断绝了?」
「当然!他当我安琪是什幺?」她嘟着嘴道:
「叫他去摸露露那一上一下的乳房好了!」
胡诚心中偷偷窃笑,如此说来,这「换情郎」的事情,轻而易举地成功了现在他祇要好好的在床上玩她一玩,她必然会对我死心塌地。
「怎幺?」她瞥了一眼道:
「你还不脱衣服,躲在这里做什幺?」
「对……」胡诚连忙开始脱衣服道:
「不应该浪费春宵。」
胡诚把衣服脱了,当脱得精光时,她上上下下地看着道
「咦,你身上没有毛?」
「怎幺,这不是毛幺?」胡诚问道。
说着,用手往下一指,安琪摇一摇头,叫起来:
「我不是说这儿的毛啊,我是说上身的毛!你没有的!」
「这不是上身的毛吗?」胡诚指头髮说。
「我不是指头髮」安琪嚷道:
「我是说胸前的毛,腰上的毛……」
「啊?浩凯脸上有鬍子,胸上有毛,腰上也有毛,这样一来,他不是成了野人吗?」
「对,他像一个野人,他完全是一个野人」她说:
「当他脸上的,胸上的,腰上的毛沾在我光滑滑的身上,擦动着,那感觉简直令人受不了……」
「原来你喜欢毛。」
「我喜欢毛给我的刺激。」她四面一望,问道:
「我们在什幺地方玩?在床上?在地上?还是在沙发上?」
啊!真是新潮,狂得像野猫。
「随你的便!」胡诚说。
安琪看了看,就在一边的长沙发上躺下来。
「这里吧!」安琪说:
「我们好好的在这里享受一下吧。」
安琪躺在沙发上,一条腿搁在沙发上,另一条腿垂在沙发边,那两条玉腿登时成了一个「L型」。
「你好像等不及待。」
「我恨!我恨!」安琪嘴巴咒道:
「我要报仇,快来吧,你的大东西,使出来啊,伸过来啊!」
胡诚笑着压到那「L」型空中间去,她的一双手已经用力地拥抱他。
她的手指在他头髮中乱摸,一双乳房在胡诚的胸前乱擦。
她的一双热烈的唇片,在他的唇上像雨点般地索吻,他被安琪吻着如山洪爆发,立即,胡诚向她进攻了。
谁知道她就在这一剎那,突然把他用力地一推。
「不!」她叫道:
「没有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
「啊!我有这幺强壮的家伙,你会说没兴趣?」
安琪伸下手来,向胡诚的鸡巴一摸,低声道:
「嗯,你的鸡巴够大,至少比浩凯大了一倍,但是我没有兴趣。」
「岂有此理,没有理由!」
「有理由!因为你身上没有毛,光光滑滑的。」
胡诚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浩凯就不同了。」安琪说:
「浩凯脸上、身上和鸡巴全是毛,刷在我身上,好痒……好痒……啊,令我心神动摇!」
「全身毛,像一头野兽,像野兽的男人,有什幺好?」
「那是刺激,他的体毛令我刺激……你身上光脱脱的,一点都不刺激,你一点毛髮都没有!」
「岂有此理!」胡诚心中骂,想了想,便对她说:
「你躺着!」
「干什幺?」安琪奇怪地问。
胡诚从沙发上跳起,转到厨房去,不一会儿,把厨房门背的鸡毛扫取了出来。
「好吧!你要毛,哦!给你毛,拿去吧。」
「啊!你做什幺?」她急叫起来,整个人一跳。
「毛啊!毛茸茸的,看。」他用鸡毛刷在她的身上,胸前,然后一直刷到她的腰上去,再往下刷。
「啊……天!」她开始拚命地推,接着她哈哈大笑起来了。
胡诚用手轻轻地刷她,手颤动着,上上下下,一直刷到它的大腿内侧。
她全身颤抖起来,又挣扎,又躲避,终于格格地大笑。
「怎幺样,这不比浩凯的鬍子要好得多了吗?」
「死东西……你真坏……」她被一刷,兴奋叫道:
「死家伙,你抱我,抱住我吧!」
胡诚用鸡毛扫前前后后的挥刷,终于她开始求饶了。
「不要这样,你……快来……跟我玩吧……来,我们一起玩吧!」
安琪变得热情如火,狠狠拥抱住胡诚。
胡诚把她拥抱在怀中,立即与安琪合二为一的呻吟着。
「啊……」安琪喃喃地道:
「原来没有浩凯……我一样可以找到其他的男人……啊!我可以找到快乐,别人一样可以让我满足。」
「当然,当然!」胡诚说:
「别人可以让你满足,而且还可以使你找到比浩凯更伟大,更巨型的……」
「对,动啊!现在你可以开始了,动啊。」她用手推着胡诚。
胡诚开始动手来,那一张沙发,开始发出「吱吱吱」的声音,大鸡巴挤进她的阴户里,感到自己好像是一具抽水机,将安琪抽动着,这动作令两人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快感。
「怕我杀人啊?」她双眼直瞪,鼻子哼了气道:「嘿!我倒希望手中有把刀,这样我就可以砍死他们!」
「天啊!」胡诚叫着:
「杀人要偿命!你杀了那个大鬍子,既不英俊又不专情,值得吗?」
她看看他,咬牙说:「谁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就去捉姦!」
「为了怕有意外,我还是看着你。」他坚持说:
「你不反对吧?」
她忍着一口气,不再说话。车子在路上兜了几个弯,到了一幢大厦前。
「我要捉姦成双!」她咬牙切齿,向大厦内走。
她走进电梯,用手一按,按了最高的一层。
「你认为浩凯把露露带回家了吗?」胡诚问她。
「当然哟!」她说:
「不然,他又何必说谎要甩开我?他不把露露带回家,难道还会在街上做爱吗?」
电梯一直升到顶楼,停住了。他们走出电梯的门。
「你怎幺进去?」他看看大门是关着,悄声问她。
「嘘───」她噤声打了一个眼色,蹑足走到门边。把耳朵轻轻地贴在门上,小心翼翼地向内窃听。
听了一会,她看看他,点了一点头。
「他在里面。」她说:
「她也在里面,他真的把露露带回来了。」
「这样……」他问:「你怎幺破门而入?怎幺捉姦成双?」
我自然有办法。」她说着俯身拾起门前的草织地垫,向地垫下一摸,摸出一把门匙来,扬一扬道:
「浩凯记性不好,常常遗失门锁!所以通常他遗留一把门锁藏在地垫下面祇见安琪悄悄地把门锁向门上的匙孔内一插,然后缓缓扭动。
大门被她打开了,两人向门内一望,祇见屋内一片漆黑。
「他们在卧室内。」安琪向灯光张望一眼,悄声说。
按着她蹑足向走廊走去,他一步也不放鬆地跟着安琪向前走。
才走进走廊,已经听到一阵女人的笑声,是露露在笑。
「你不要乱摸嘛……嗯……你看你……嗯……」露露咭咭地笑:
「啊,你摸得我全身毛孔都发痒了,哈哈哈……」
她靠近墙,一点一点地走近房门。
这房门,是半开着,灯光与声浪从里面洩出。
两人向门缝内张望着。
不望犹可,一望之下,安琪气得全身发抖,她的手紧紧地抓住他的手。
祇见露露全身脱光光的躺在床上,浩凯也脱光了衣服,像一头野兽。
他伏在她的身上,用手在轻轻抚摸露露的双峰,又搔她的小腹。
「你坏……你坏……」她边笑边叫:
明知道人家怕痒,你还偏偏搔人家的痒……你好坏……你好坏。」
咭咭咭」地,她又发笑了。
「你那个安琪怕不怕痒啊?」露露问那个鬍子说:
「她又怎幺能受得了你这样的触摸啊……啊……嘻嘻嘻……」
「安琪不怕痒!」浩凯回答道:
「安琪啊!她最怕这一个。」
「怕什幺?……」
就在这时,浩凯的头低下去了。
他脸上的鬍子触在露露的身上。
他上上下下地移动他的脸,鬍子就在她雪白的身躯,上上下下地扫动着。
「……啊……啊……痒……痒……」露再也忍不住了,全身颤动起来。
「安琪最怕这一个……你也怕吧?……哈哈……」他发出笑声:「───所以,安琪最喜欢我的鬍子……哈哈……」
浩凯笑得发狂,安琪的手紧抓在胡诚的手臂上,用力的紧捏着。
她气得再也受不了了,若她的手中有刀,真的会在这一刻杀进去的。
「你不要呵我痒,要来,来吧……」
说着,露露的手就向浩凯的颈上一勾,两条腿已缠到他的腰上去了。
露露的腿很长,线条均匀,脚趾涂上的粉红色,在灯光中闪闪发着亮光。
浩凯吐了大量的唾液,用手涂抹着他的阳具。
「好吧,来,来……」浩凯把他的身子一挺。
身边的安琪,忽然在黑暗内失了蹤,他发现她不在身边,想去找寻,但是房内的景色又如此吸引人,只是目不转睛地呆看房内的一切。
祇见浩凯咬着牙龈,向他身上的露露进攻了。
就这样地,他们两个人合而为一了。
「哦!我的浩凯,我的凯哥……」露露淫叫着。
「哦!我的凯哥,我的哥哥……」露露双手拥着浩凯,嘴里不断在叫着:「我的凯哥……我的浩凯……我知道你虽然跟安琪在一起,但是你始终是爱我的……」
浩凯祇管自己拚命地冲刺,嘴里一句话都不说。
「浩凯,浩凯!」露露说:
「你什幺时候跟安琪摊牌!什幺时候跟她断绝?」
「断绝!哼,现在断绝!」突然间,安琪的声音大声叫。
胡诚一回头,祇见安琪从浴室取了一条橡皮管,橡皮管的一端接着水龙头,另一端,正溅着水柱。
她咬牙切齿地,用脚把房门「呯!」地踢开。
床上的浩凯和露露一呆,大声惊叫起来。
就在这一剎那,安琪手中的水喉向他们身上乱射。
「死男人!死女人!」她狂声遽叫道:
「我要你们好看!狗男人,要你们好看!」
两个光脱脱的人滚在床上,一身是水。
这情形就像在街头交合的一双野狗,被人淋了一身冷水一样。
「安琪……安琪……你不要……你不要……」浩凯在床上,一面用手挡着水柱,一面哀叫。
「从此以后你不要叫我!不要再找我,我不会再见你!」她把水喉向他们一扔转身就走。
胡诚见到床上的两人一副狼狈相,就忍不住想笑。
安琪这时候已三两步的走出房子去,胡诚想了一想,立即匆匆追赶。跑到外面,他们乘电梯下楼,到了楼下,她就忍不住呜哭起来了。
「他欺骗我……」她哀声说:
「我一向这幺爱他……他竟然欺骗我……」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送你同家去吧。」
突然她把脚一踢,狠狠地说:
「我不回去!我不回家!」
他呆怔怔地问:
「你不同家,要到什幺地方去?」
「嘿!这样是便宜了他们!」她咬牙切齿地道:
「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这用不着去报仇,安琪,最好的方法是,你也同样去做……」
「怎幺同样去做?」
「当然嘛,他能跟别的女人偷情,你也跟男人偷情。他跟女人做爱,你也同样与别的男人去做爱。」
她醒了醒鼻子,好像一个迷了途的小孩子。
这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了,也是最适合下手的时刻了。
「既然不想回去,就到我家里去坐坐吧!安琪。」
她的一双眼睛瞪了一眼,想了想,没有出声。
这时候,它是最没有主张的时候了,就得乘机「进攻」。
一辆计程车迎面驶来,他伸伸手,把那部车子叫停了。
「还不上车,半夜三更站在路上多冷,快,跟我上车吧!」
他不给安琪有时间思想,立即就把她一拉,拉上车子去。
到了胡诚家,安琪整个人好像一个木头人,呆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胡诚泡了一杯咖啡给她,把咖啡杯子交到她手中。便道:
「喝咖啡吧,提提神!」
她拿着咖啡杯,把杯子移到嘴唇,喝了一口,然后,她喃喃地说:
「嘿!没有这幺容易!臭男人,我讨厌他的鬍子!他的臭鬍子!讨厌,讨厌!」
女孩子真奇怪,刚才还爱得他的鬍子要死,现在又骂他的鬍子是臭鬍子。
胡诚道:
「放过他们算了。情郎嘛,有什幺了不起?这个对你不好,再换一个好了!是不是?」
她又喝口咖啡道:
「───我要报仇!」
「用刀去宰他?」胡诚问道。
她把咖啡杯子放下,突然,她双手向自己的上衣一放。
「吱!」地一声,她的上衣被解开了,他的眼前立时一亮,祇见到一双皙白的乳房在胡诚面前跳跃着。
这一双乳房,形状如此地美好,尖端微微地翘起,好像一只雕刻出来的艺术品一样。
她把上身一扭动,这双乳尖在微微地慢动着,充满着弹力。
「你…?」他呆呆地道:
「……做什幺……安琪?」
「你说,你说,胡诚!」安琪连声问道:
「这一双乳房,美丽吗?」
「美丽……」他喃喃说:
「当然美丽……」
她接着站起身来,脱她下身的衣服了,这一下,可把他吓坏。
「你做什幺,安琪?」胡诚道:
「你跳脱衣舞?」
「我脱衣服!」她叫:
「我给你看,你认为我的身段美不美丽?那个死浩凯竟然会对我生厌……我才不相信!你看!你做个公正!你看,我这副身材,是不是比那个臭露露美?你看!」
边说,她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了下来。
「你看!」她光脱脱立在胡诚面前,一撑腰道:
「你不认为我此露露美丽吗?」
她的身材比任何银幕上的性感尤物更是诱惑人,她身上每一条曲线,均匀得好像画家笔下的裸女像。
「怎幺样?」她很不服气地问。
「好极了!」他非常欣赏地道:
「简直是……该大的地方大,该小的地方小……多一分嫌多,少一分嫌少。」
「嘿,那个露露,怎能跟我比呢?」她嘟一嘟嘴道:
「她的一双乳房,就一高一低。」
「有次她自己告诉我的。」她讲:
「所以她穿乳罩时,一边的吊带就要束得特别地高,把另一边吊起来。」
看看她,忍不住笑起来,安琪完全是气得昏了,嘴巴乱讲。
「浩凯这东西,竟看上她!」她越说越气。
「胡诚不明白这意思。」想了想,便问她。
「浩凯明天打电话给你,求求你和好。」胡诚试探着问。
「你会怎幺样?」
「怎幺样?」安琪叉叉腰,嘴中咒骂起来:
「──我放他的屁!」
「这样……你是跟这个浩凯断绝了?」
「当然!他当我安琪是什幺?」她嘟着嘴道:
「叫他去摸露露那一上一下的乳房好了!」
胡诚心中偷偷窃笑,如此说来,这「换情郎」的事情,轻而易举地成功了现在他祇要好好的在床上玩她一玩,她必然会对我死心塌地。
「怎幺?」她瞥了一眼道:
「你还不脱衣服,躲在这里做什幺?」
「对……」胡诚连忙开始脱衣服道:
「不应该浪费春宵。」
胡诚把衣服脱了,当脱得精光时,她上上下下地看着道
「咦,你身上没有毛?」
「怎幺,这不是毛幺?」胡诚问道。
说着,用手往下一指,安琪摇一摇头,叫起来:
「我不是说这儿的毛啊,我是说上身的毛!你没有的!」
「这不是上身的毛吗?」胡诚指头髮说。
「我不是指头髮」安琪嚷道:
「我是说胸前的毛,腰上的毛……」
「啊?浩凯脸上有鬍子,胸上有毛,腰上也有毛,这样一来,他不是成了野人吗?」
「对,他像一个野人,他完全是一个野人」她说:
「当他脸上的,胸上的,腰上的毛沾在我光滑滑的身上,擦动着,那感觉简直令人受不了……」
「原来你喜欢毛。」
「我喜欢毛给我的刺激。」她四面一望,问道:
「我们在什幺地方玩?在床上?在地上?还是在沙发上?」
啊!真是新潮,狂得像野猫。
「随你的便!」胡诚说。
安琪看了看,就在一边的长沙发上躺下来。
「这里吧!」安琪说:
「我们好好的在这里享受一下吧。」
安琪躺在沙发上,一条腿搁在沙发上,另一条腿垂在沙发边,那两条玉腿登时成了一个「L型」。
「你好像等不及待。」
「我恨!我恨!」安琪嘴巴咒道:
「我要报仇,快来吧,你的大东西,使出来啊,伸过来啊!」
胡诚笑着压到那「L」型空中间去,她的一双手已经用力地拥抱他。
她的手指在他头髮中乱摸,一双乳房在胡诚的胸前乱擦。
她的一双热烈的唇片,在他的唇上像雨点般地索吻,他被安琪吻着如山洪爆发,立即,胡诚向她进攻了。
谁知道她就在这一剎那,突然把他用力地一推。
「不!」她叫道:
「没有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
「啊!我有这幺强壮的家伙,你会说没兴趣?」
安琪伸下手来,向胡诚的鸡巴一摸,低声道:
「嗯,你的鸡巴够大,至少比浩凯大了一倍,但是我没有兴趣。」
「岂有此理,没有理由!」
「有理由!因为你身上没有毛,光光滑滑的。」
胡诚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浩凯就不同了。」安琪说:
「浩凯脸上、身上和鸡巴全是毛,刷在我身上,好痒……好痒……啊,令我心神动摇!」
「全身毛,像一头野兽,像野兽的男人,有什幺好?」
「那是刺激,他的体毛令我刺激……你身上光脱脱的,一点都不刺激,你一点毛髮都没有!」
「岂有此理!」胡诚心中骂,想了想,便对她说:
「你躺着!」
「干什幺?」安琪奇怪地问。
胡诚从沙发上跳起,转到厨房去,不一会儿,把厨房门背的鸡毛扫取了出来。
「好吧!你要毛,哦!给你毛,拿去吧。」
「啊!你做什幺?」她急叫起来,整个人一跳。
「毛啊!毛茸茸的,看。」他用鸡毛刷在她的身上,胸前,然后一直刷到她的腰上去,再往下刷。
「啊……天!」她开始拚命地推,接着她哈哈大笑起来了。
胡诚用手轻轻地刷她,手颤动着,上上下下,一直刷到它的大腿内侧。
她全身颤抖起来,又挣扎,又躲避,终于格格地大笑。
「怎幺样,这不比浩凯的鬍子要好得多了吗?」
「死东西……你真坏……」她被一刷,兴奋叫道:
「死家伙,你抱我,抱住我吧!」
胡诚用鸡毛扫前前后后的挥刷,终于她开始求饶了。
「不要这样,你……快来……跟我玩吧……来,我们一起玩吧!」
安琪变得热情如火,狠狠拥抱住胡诚。
胡诚把她拥抱在怀中,立即与安琪合二为一的呻吟着。
「啊……」安琪喃喃地道:
「原来没有浩凯……我一样可以找到其他的男人……啊!我可以找到快乐,别人一样可以让我满足。」
「当然,当然!」胡诚说:
「别人可以让你满足,而且还可以使你找到比浩凯更伟大,更巨型的……」
「对,动啊!现在你可以开始了,动啊。」她用手推着胡诚。
胡诚开始动手来,那一张沙发,开始发出「吱吱吱」的声音,大鸡巴挤进她的阴户里,感到自己好像是一具抽水机,将安琪抽动着,这动作令两人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快感。
「怎幺?你感觉如何?啊!是不是比浩凯大?」
「对,对!」她一直喘气,不断地点头道:
「对,对,此浩凯大。」
「是不是比浩凯强?」
「是,强多了。」
「这样说──」胡诚笑了笑道:
「我比浩凯好很多,你又何必要浩凯。」
「对,对,我又何必要浩凯?」她断断续续地嚷道:
「那死东西,那没有良心的东西,我不要他了!」
「你,我令你快乐,给你无上的享受,就是不要浩凯!怎幺样都不要再找他!」胡诚边咬牙切齿地说,边尽力地干。
他们好像波浪一般地一起一伏,那沙发开始「吱吱吱」地叫了起来,发出声响。
「现在我不要其他的男人了!我不要浩凯了!」安琪的手紧紧地抱住胡诚,她挺起腰,尽量用她的腰顶着他的身体。
「这样最好,你祇要一个……一个我,就已经够了。」
「啊……」她急急匆匆地叫:
「对,对……那死没有良心的,我不再要他了,啊!你真令我快乐!」
经过一场大战,安琪躺在沙发上。
她的腿合拢了,再也不像是那个「L」字形状,她全身鬆软,好像一团糯米粉,又好像是一团溶蜡一样。
胡诚从安琪身上爬起,喘了一口气,然后低头看了看她。
安琪不断喘息,一上一下地,她已经完全鬆散了。
「你怎幺了?」胡诚挥挥手,低头看着她说:
「好像一头斗败了的野兽!」
「啊……我给你快要弄死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道:
「从来没有男人……像你这样……浩凯也从来不会这样……你在拚命……」
「我要令你欢心。」他用毛巾围绕自己的下身,笑着说。
「你要我的命」安琪叫道:
「你令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了。」
「你大概未见过像我这幺强的吧!」胡诚说。
她闭上双眼,极力将自己平静一下,然后向胡诚伸伸手。
「给我一支香烟吧!」安琪说:
「让我鬆一口气。」
「唉!这幺小的年纪,就抽烟。」
「嗯!抽烟有什幺稀奇。」安琪耸一耸肩道:
「刚才我还抽大雪茄,不是吗?」
胡诚忍不住格格地笑起来,拿出香烟点了火,吸了一口,便把香烟递给安琪。
安琪接过烟,深深的吸了一口,冒出烟,然后看看胡诚。
「怎样?现在已向浩凯报了仇吧!一个浩凯,有什幺了不起,一脸的臭鬍子,看看我,那点输他呢!刚才那一套,他就不是我的敌手。」
安琪咬咬唇角,忽然微笑起来,胡诚趁机伸手,把她抱住了。
两人又吻在一起了,他的手拿着鸡毛扫,又轻轻的在她身上拨动。
「啊……啊……」她急叫起来:
「啊……毛,毛……毛啊!」
这一次,她在胡诚手中了,周太太的这笔钱,不在他手中才怪。
胡诚点着了一只烟,然后看着周太太。
周太太雍容华贵地坐在胡诚面前,她看他吸烟,神色是凝重的。
「我的女儿是跟浩凯断了。」周太太说:
「她再也不去那间什幺『小屋』夜总会了,也不再提起浩凯了……」
「对!」胡诚抽口烟,点了点头道:
「现在安琪不再跟浩凯在一起,不过,她是跟我在一起,我说过,要她与浩凯分开,易如反掌!」
「对!不过,现在我们要谈谈我们的事了,现在要求你和安琪分手!」
「嗯!」这一次,胡诚望望天,看了看周太太道:
「周太太,你女儿现在对我死心塌地,难分难解了。」
周太太瞪着胡诚一眼,便道:
「这是你的本事,不过,我们早已说好,把浩凯甩掉后,你就和安琪分手。」
「这样好吧,但是我要五十万元!」
「五十万?」周太太双眼一睁,急说:
「这明明是勒索。」
「不是勒索,是条件。不然的话,我跟安琪打得像炉中的铁,又红又辣,你是管不了……」
「啊……你……」
「如果你不答应,我就决定和安琪相处下去,我发觉她很漂亮,而且,她那天必然会愿意嫁我……」
「你……你……」周太太气得双眼上翻,抖动着声音说:
「你怎幺可以趁机敲竹槓呢?」
「这不能说是敲竹槓,因为事前我不知道安琪是如此动人,如继续下去,将来娶了她,还会少于这五十万元吗?」
周太太咬牙切齿,心中已愤怒到了极点。
但是胡诚仍然缓缓地抽烟,优哉地说:
「我已约了安琪半个钟头后在此见面,周太太,你是要我和安琪再交往,还是要我立即走路,就看你的意思了。」
周太太心中一百个不愿意,但是想了想,只好打开皮包,拿出一把钞票和支票簿。她严肃地说:
「这是现金二十万元,我再填一张三十万的支票给你,你立刻和安琪分手。」
胡诚接过了现钞及支票,礼貌地向她点了点头道:
「周太太,相信我的从业良心,我绝对不会再和安琪有任何瓜葛,安琪的出身好,你们该细心教导她。」胡诚看周太太紧闭着嘴,于是又说:
「安琪马上就要到了,我先走,祝你一家团圆。」
胡诚到银行领了三十万元,将房租、电话费、会钱及向朋友借来的钱,全部还光。同时买了一只十二万元的金錶,剩下的钱就留在家中。
晚上,胡诚穿着最高级的西装,出现在「豪门」大酒店。
这是一家社交名流出入的贵族场合,他向侍者要了一瓶「三星」,独自浅尝着。
双眼四面望望,见到不远的小桌上,有一个女人正向她瞄眼色。
这个女人,一件大红色的晚礼服,脸上涂着妖艳的化妆品。
看看她,嗯!手上倒还有些首饰,她的手錶好像是「伯爵」。看她的样子,好像是一个怨妇。
说她是妓女,不像,一般妓女好像没有她这样的气派。
她边喝酒,边看着胡诚,他把香槟杯子举起,向她举了举杯──这是一种试探。
她笑了笑,也举起杯子来──有反应了,好像电报机,打过去,她拍过来,算是有些「接触」了。
胡诚瞥她一眼,唇角微微一笑──她的唇角也微微一笑。
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看情形运气不错,下午才进了钱,晚上又可以跟这个红衣艳妇欢乐一个今宵了。
他拿出香烟,点着了一枝。
那边,那红衣女郎也拿出了香烟,但是她却没有点火,她那一双眼睛向胡诚瞄啊瞄过来。
胡诚是聪明人物,一见到这个情形,立即走到她的身边去。
「康!」一声,胡诚为她点燃了烟,她大方地笑了笑。
「这里的气氛真好。」他打开话题:
「又热闹!」
「嗯!」她用优美的姿势喷出烟来。
「一个人?」胡诚问道。
「是的。」她浅笑着:
「你呢?」
「那还用说。」胡诚又倒了杯酒,同她举着道:
「我叫胡诚。」
「哦!很斯文的名字,模样也俊。只是你一个人如何渡过这漫漫长夜?」
「对!漫漫的长夜,你有什幺好主意没有?」
「我独自喝酒。」她说: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想,最好找一个英俊的男人,谈谈天,喝喝酒,大家『罗曼蒂克』一下子,怎幺样?」
「嗯!『罗曼蒂克』一下子,我十分赞成。」
「好吧!」她说:
「你愿意和我谈谈吧?年青人。」
「乐意得很,谈什幺事情?」
「譬如──」她耸耸肩道:
「先说说你自己吧!不过,我们虽然只是萍水相逢,大家都最好说真话。」
「对!我说真话,你想知道一些什幺?」
「你是一个神男吧?」她压低声音问。
胡诚一怔,接着说:
「我祇听过神女,可没听过神男。」
「不叫神男──」她想一想道:
「那幺,叫做舞男吧?」
「我又不是整天跳舞,舞什幺男啊?」
「那幺──」她思索一下,又接着说:
「叫做妓男吧?」
「我听过妓女,没听过妓男。」
「啊!对了,应该倒过来说,叫做男妓,不是妓男。」她恍然大悟地。
「这又如何?」
「不妨承认好了。」她说着,十二分感兴趣地道:
「我对你们这种男子,十分兴趣。」
「你是什幺杂誌的记者?还是作家,或者是警探?想来调查我?」
「我想深入地知道你们的生活。」
「什幺事?」
「遇到了,彼此先论价啊,讲好了价钱,就讨论上哪一张床,她的?我的?还是酒店中的?」
「然后呢?」
「当然上床啊!上了床,要嘛我在她上面,或者她在我上面……还有什幺呢?」
「有没有免费做的?」她闪闪眼睛,又问我:
「好像,不收费的。」
「你走到饭店去吃饭,有没有吃饱了肚于,而拍拍屁股就走的?」
「对!」地想了想:
「必须付钱。」
「这就是了。我们的宗旨,出一分力,赚一分钱,对不对?」
「有没有人事后赖帐的?」她忽然异想天开地问。
「不会吧?我总有办法把她们的钱逼交出来。」胡诚道。
「嗯!」她想了,又道:
「──倒是很有趣。」
「什幺有趣?这祇不过是一件生意而已,就好像你们女人拿钱到菜市场去买菜一样,你给钱,我给货。」
「嗯……」她闪闪眼,道:
「我很有兴趣,又十二分的好奇。」
「有兴趣,又好奇,要不要试一下?」
「你会收我多少钱?」
「五仟吧!怎幺样?」胡诚回答说。
「太贵了。」
「铁价不二。一试之后,你就知道,不是吹牛,令你欲仙死,如癡如醉……」
「你这个人很聪明。」她笑笑道:
「而且还有一张会说话的嘴巴。」
「嘴巴之外,还有一条十分有用的舌头。」
她会意,突然之间「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
「要不要试一下?我们两个人,来个『罗曼蒂克』一下。」
「嗯!」她想了一想:
「───我要一会儿打一个电话……才能决定。」
「为什幺?」
「要看我的丈夫,回不回家。」她说:
「有时候,他通宵不归,那幺,我就可以与你『罗曼蒂克』一下子。」
「介意我问你几个问题吗?」
「你问好了。」
「你丈夫是做什幺的?」
「赌!赌鬼!」她说:
「一天到晚赌,把妻子冷落在香闺!」
「难怪你一个人出来逛,闷闷不乐,独自喝闷酒了。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子,你遇到了我。」
「怎幺幸运?」
「从现在起,你就找到乐趣了,以后,你让你的丈夫去赌,趁他出去时,就来找我,在我家来个『罗曼蒂克』一下子,哈哈哈,怎幺样?……」
「我去打一个电话。」她说:
「看看他在不在朋友家里赌,如果他在赌钱,那时候……我们才再说呀!」
她说着,站起来去找电话,胡诚只有再度独饮。
乐队只演奏半个曲子,那女人就回来了。
「我的机会来了,运气不错!」她笑瞇瞇地说:
「我的老公去赌了,他一赌,哈哈!不到天亮是不回家的。」
「那就好极了!我们可以好好的『罗曼蒂克』一下了。」
「你的家?」她悄声问道:
「还是我的家?你说!」
「我看,你的家,你认为怎幺样?」
「好的!」她说:
「我的家。」
「对了!你贵姓大名?我忘了问。」
「大妞。」她回答着:
「人人叫我大妞,你也叫我大妞吧!」
胡诚和大妞下了车,两人手挽着手,她把整个身子靠在他的身上。
「你家中没别人吧?」胡诚问道:
她摇摇头,带他进大厦,他们进了电梯,坐上楼层去了。
她的身体胸前堕着两包大米袋,胡诚问她:
「不辛苦吗?」
「女人,有什幺办法?」大妞摇头道:
「其实,你们男人那儿吊着那东西,走起路来挥啊动的,不也一样辛苦吗?」
你不觉得胸前很沉重吗?」胡诚问道。
「你自己也不觉得那儿沉重吗?」大妞马上反问着。
这时令胡诚哈哈大笑起来,她见到他笑,大妞也大笑了。
电梯到了顶楼。
她开了门,里面是一个很舒适的客厅,大妞的家虽然不怎幺豪华,但让人感觉很舒坦。
看样子,她的丈夫有点钱。
大妞把手皮包一扔,又把鞋予一踢,关上门,伸手拉住他。
立即,大妞两片唇已热辣辣地印在胡诚的唇片了。他从末见过女人这幺「性」急的,这一次,她真是迫不及待了。
「你要不要喝杯东西呢?」大妞问道:
「我看,还是先上床吧。」
「这幺急?」
「若是不急,我找你回来干什幺?」她告诉着:
「我的丈夫迷恋赌,他赌得天昏地暗!我呢?迷恋男人那吊着的东西!来嘛,快来!」
大妞拖拖扯扯,把胡诚拖到一边的房间去。这房间大概是她的睡房吧?」
里面有张床,也没有亮灯,看不清楚四周的情况。
就在这一刻,她突然将胡诚向前一推。
他失去平衡倒下去,直跌在床上,弹簧床将他上上下下地弹动了几下。
大妞似飞禽般向胡诚一扑,扑在他身上,好像是一只狐狸。
按着她的一只手在乱摸了,首先摸他的头髮,然后再摸胸口,不一会,她的手已摸到她的腰腹上了。
她大概等急了,像一个从沙漠中旅行出来的灾民,缺乏食水,急于要找水源似的。
她的手乱摸乱索,一下子就到了他的腰以下。她是十分熟悉「地区」与「位置」的,一摸一抓已把她所想要的物件抓在她的手中了。
「啊!」她低声说:
「还好,是直的。」
大妞的手指边摸边说着,胡诚有点莫名其妙。
「什幺直的?男人这地方,当然是直的。」胡诚说着。
「不,不,不。」大妞连声说:
「不,男人不是全直的。」
「你见过弯曲的吗?」胡诚问道。
「我老公就是弯的。」她触摸说:
「月儿弯弯照九州。」
「不会像月儿弯弯吧?」胡诚说。
「弯!比月儿更弯!」她用手比一比道:
「啊!对了,好像一把弓一样!」
「哇!一把弓,是……这样弯一弯,再那样弯一弯……哇!那是弯两弯了!」
「对的,就是弯了又再弯!」她笑瞇瞇地说:
「所以,与我合在一起,我是曲了又再曲!」
「怎幺可以?」胡诚问道。
「所以我永远不满足啊!」大妞说:
「今天,我真是幸运,找到了一个直的。好直,好直,好像一支笔。」
「就祇是一支笔吗?」
「像一枝枪。」
「比枪大点吧?」
「一头炮。」大妞用手比摸着:
「对,开始时像笔,刚才像枝枪,啊……现在,大了大了,现在像炮了!」
她哈哈地传来一阵笑。
「你快点干我吧!报上登载,最近有几个女人,把一个男人强姦了。」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在强姦你。」她发起狂来,双手迅速地把他身上的衣服解开。
他也用不着动手,她一下子已把胡诚剥得光光的。
她转过身去,很快地把自己的衣服也脱下了。
胡诚看看她,这个大妞脱下衣服,要比穿着衣服好看得多了。
她的一双大乳房,看来十分的自然,当然不是打针加大的。
她向床上的胡诚一看,他把自己的手脚张开成一个「大」字型。
「你做什幺?」她问:
「成个大字型。」
「我现在是『太』,不是『大』字型!别忘了,我那儿还有那幺的一头炮哩!」
「真奇怪!」大妞嚷道:
「你成『太』字型的躺着,做什幺?」
「欢迎强姦我!」
她哈哈地又传来一阵笑声。接着,她一只脚向他身上跨来。
她骑上来了,对準目的物,她缓缓的向他身上一压。
「啊……」她低声呼叫:
「好直!好直……不是月儿弯又弯……好直,好直的啊……」
她边叫,边把胡诚「强姦」了。
大妞又喘气,又流汗。她娇呻着,从他身上跌了下来。
接着,她重重地喘气,身体一动不动,完全好像鬆软了。
她双眼紧闭,一动不动,他吓了一跳,坐起身来,用手摸了摸她的鼻孔。
她的鼻孔仍有气息,于是他又用手把一把她的脉搏。
她的血脉仍然在跳,而且跳着很急速!他这才鬆了一口气。
「既然无力,刚才又何必那样拚命?」
她一句话也没说,儘是缩在那儿,好像晕死过去一样。
他摇摇头,歎口气,爬起身来,把她独自扔在床上。
胡诚进了浴室,亮了灯,扭开浴室内的莲蓬,开始洗澡。
洗了一个澡,感觉全身轻鬆,体力又回复了。
精神百倍之后,又用毛巾抹乾了身子,穿好衣回到卧室。
大妞仍然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看看她,又看看时间。
现在应该走了,趁她老公未回来离去。
离去前,胡诚自然向她要报酬。
「大妞。」
她双眼紧闭,一动也不动。
「大妞……」他又叫。
她仍然躺在那儿,这时候,他用手推一推她,对她说:
「喂,你是真睡,还是装睡,睁开眼!张开眼睛!」
大妞被他这一推,才缓缓地睁开双眼道:
「你做什幺?」
「我被你干完了,现在要走了。」
「好吧!」她又闭上眼睛,向胡诚挥挥手说:
「那幺再见!拜拜!」
他听了一怔,想了想,岂有此理!她姦完后,但未付款哩!
「大妞,你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情吧?」
「我等一下会洗澡,你不用提醒我。」她闭眼说,
「洗澡?谁管你洗澡?你忘了,五千元的代价尚未付款哩!」
「五千元?」她睁大双眼:
「谁说要付你五千元呢?」
「大妞!」他一怔,呆呆地说:
「你在开什幺玩笑?」
「刚才的事,你和我一样地享受,又兴奋!」大妞说:
「为什幺我要付你钱?真是莫名其妙。」
「笑话!」他顿时翻脸,指指她道:
「我不怕别人赖帐,你知道我是做什幺。」
「男妓。」
「对!就从来没有人玩了我,再我身上赖过帐,你如果不乖乖付款,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小伙子!」她不但不怕,反而摇摇头道:
「我大妞是什幺人,也不弄清楚?我不怕你,不付,就是不付。」
「你敢?」他说着,就立看身子向她的床上一坐:
「──我现在,不走了,看你怎幺样?」
「看我怎幺样?」她忽然笑起来,摇摇头道:
「我这儿任你搜,也搜不出五千元来!」
「你存心不给!骗我回家?」他可生气了,大声叫:
「──好哇,现在我不走!除非,把你带的名贵手錶、戒指全拿出来交给我抵押。」
「笑话,天下大笑话!」她双手撑腰,对他大笑。
「你笑好了!我坐到你老公回来,看看是你笑,还是我笑?」
「我现在笑。」她一点不着急,缓缓说:
「──一会儿我老公回来,我就哭。」
「啊……你哭?」他听了一呆。
她已从床上坐起,取起地下自己的衣服,抓在手内,乱扯乱撕……直至她把衣服撕得粉碎为止。
「你做什幺?」他惶恐地问。
「你反正光脱脱在这儿,那更好,人证物证全在!」她说:
「我等会就大哭大叫,说你强姦我……非礼我,向我施暴……」
「啊?」他顿时一呆。
「你在电梯内跟蹤我,逼我进门,再强暴我!」她大声说:
「嘿!我要报警,告诉我的丈夫!也许,你该看看我丈夫是什幺职业吗?」
她边说边跳到墙边,一手按亮墙边的电灯。
胡诚抬头一看,墙上悬挂着不少照片,还有锦杯,上面有斗大的字样,「一九九二年拳击冠军!」
「啊……」他吓得脸上发青。
「你慢慢等他回来吧。」她哈哈大笑:
「我现在笑,等会儿哭!看我老公怎样处置你。」
胡诚发觉她真的不是开玩笑,知道今天是倒了霉运!天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先跑为妙。
他嘴里骂着粗话,匆匆穿起衣服及鞋子。
正準备奔向门口时,大妞忽然娇叫一声:
「慢着!」
「什幺事?」
「刚才我看你手上带的手錶,很名贵、又新式。」大妞眼光一闪,伸了手说:
「把它脱下来放在桌上。」
「你……你想打劫?」胡诚大声叫。
「正是如此。」大妞说:
「不然我按警铃,叫楼下的管理员上来,说你劫色,怎幺样?脱不脱手錶?」
胡诚大叫一声,觉得双腿已鬆软了!
于是把手錶脱下给她,拔腿就跑了!
********************************
经过那次事件后,胡诚决定要换个环境,避免被那件事所干扰着。
他来了高雄,由于初到这环境,对一切都很陌生,离开了自己老窝,重新努力,期望能够建立起知名度。
经过一阵子的努力,他终于建立起声誉了。
在高雄的牛郎圈子里,不是说大话,胡诚的名气是数一数二的了。
这得归功于生来就有强健体魄和自认不错的男性脸孔。
他的收入不能算不丰,因他在穿着、吃喝方面的花费也不少。
这一次要服务的对象是个外国女郎,由旅行社的小吴介绍的。
这天,胡诚在机场出口,看经过海关的旅客全走光了,看看手錶,皱起了眉头。
电视板上的班机是对的,时间也没有错,他仔细观察每个从海关走出来的旅客──祇是没有那个金髮的伊丝。
他将照片从口袋内取出,看看照片上的那张脸,大约二十五岁,长长的金髮,脸上有轻微的雀斑。
曾经从他身边走过的旅客,没有一个是金髮的。
现在机场的旅客全走开了,他把照片放进袋内,失望地推开玻璃门走出。
小吴一定把班机弄错了,于是胡诚走出机场,準备回去时,看到一对年青的夫妇在路边等着焦急万分。
那个女的,黑色的短髮,明亮的眼睛,脸上没有雀斑。
她穿着一套黑白相间的衣服,阔阔的长裤。
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一头金髮,很年青,穿着红白色的新型服装。
他们的行李全放在路边,不断地看着手錶,不断地往路面望去。
胡诚走过他们身边要到停车场去,那个女人突然笑了笑,走过来了。
「请问你──。」她开口用英语问:
「这儿是乘搭『的士』的地方吗?」
「是的!」胡诚点点头。
看见她身边的男人,也正向他笑笑。
「一架车子也没有。」她焦虑说。
「等一会儿会来的。」
「你有车子?」她急急问。
「是的!」
「这儿到高雄市区多远?要多少车资才够!」
「不远!车资便宜。」
「你有车子,可以载我一程?」她进一步问,一点也不拘束地。
「对不起,我的是跑车,只能坐两个人,不能带行李。」
「至少你能带我们先到酒店去。」她说着,便转头介绍道:
「喔!他是我丈夫伊雷。」
那个金髮青年向胡诚点点头。
他的妻子转头与他讲起话来,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什幺语言,迅速含糊,胡诚听一会,一点都不明了。
不一会儿,那个黑髮的女人回过头来,高兴地说:
「好了!先生,你可以载我一程了。」
「什幺?」
「我丈夫同意,让我先坐你的车子到酒店,然后他带行李叫『的士』到酒店。」
胡诚不明了地瞪住她看,她转身向丈夫挥挥手。
「我们可以走了,车子停在什幺地方?」她边说边将手插到胡诚手臂里。
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一时他不知道怎样去拒绝……。
车子开过闹市,她坐在身边,不停的看看胡诚。
「麻烦你!」她笑笑说:
「本来我是有人接我的,但是……也许那个人失约了。」
「对方失约了?」
「你叫什幺名字?」她问。
「胡诚,你呢?」
「伊丝!」
「你是瑞士人?你就是伊丝?」胡诚愕然地大叫起来。
「你是……」她惊讶地道:
「你是旅行社小吴先生介绍的……?你怎幺不早说?」
「我有你的照片,是金头髮的,但是你不是,我怎幺说呢?」
「哦!女人是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她畅快地一笑,将手往头上一拉。
她把头髮拉下来,露出里面闪闪发光的金髮。
「你戴的是假髮?」
「世界上的人真奇怪,黑髮的喜欢金髮,金髮的喜欢黑髮。」
「那个……是你的丈夫?」
「嗯!」她爽直地点头。
「你有丈夫又怎会……?」胡诚看看她一笑,又说:
「你知道我是什幺样的人?」
「你是要有代价,令女人开心的人。」她回答,一样爽直。
「你的丈夫呢?他会怎幺想?」
「他不会介意。嗯!小吴眼光不错,你够英俊,我真喜欢你,体格好吗?」
「体格?」
「你真不知道我的意思?」她垂下眼,看看我裤下……
「我说的是那方面的。」
「你有软尺吗?可以动手量一量。」
「我行李内有软尺,回酒店再说吧!」她嫣然一笑。
她订的房间在十楼,既然找到僱主,就陪她上楼去。
进了房间,是一间双人房,两张床分开的双人房。
胡诚靠在墙角默默地看着她,实在不明白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她既然已有丈夫,为什幺还会到高雄「租」一个这样的情人?
她和丈夫明明在机场一起等车子,她丈夫又怎幺肯这样慷慨让她坐胡诚的车子。
胡诚一点都不明白。
她站起来了,走到胡诚面前。
她向胡诚身边一靠,神秘地笑着,右手一垂,凑过头摸他的小腹。
她预计位置的準确,一摸一抓,已把目的物接住。
「你不能等丈夫把软尺带来才量吧?」
房门忽然被打开,胡诚看见那个叫伊雷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提行李的侍童。
伊丝的手竟然没有放开,仍然紧紧的抓着胡诚裤下的目的物。
胡诚心中一惊,忙将身子一转,背面向她丈夫,急急忙忙把她的手拉开。
这时伊丝转身跟丈夫叽叽咕咕的讲话。
侍童把行李放下,伊雷取出箱中的衣服,向浴室走去。
浴室的门关上后,伊丝又走过来了,这一次她用手指指胡诚的鼻尖。
「你很怕我的丈夫呢?」她大声道:
「嘘──」他用手指在唇口一比,示意她禁声。
「等我丈夫走后,我们做爱。」她仍然大声道:
「我每次会照付钱给你的,可不能偷懒。我很久没有快乐了。指的是性方面的快乐。」
「喂!别这样高声讲话,他能听到。」
「我丈夫?不会,他根本不懂中文,我们儘管讲,他赶着要出门。」
她轻鬆的笑说。
胡诚鬆了一口气,坐下了。
伊丝很感兴趣坐到胡诚的身边来,靠在他的肩上,一手拉开他的裤链。
「喂!你?」
胡诚很快地感觉到她尖尖的十只手指已经接触在他最私有的性器上。
他用手去挡,伊丝已经将胡诚从衣服内提了出来。
「嗯!你有这种条件,难怪能出来赚女人的钱。」接着又说:
「你知道吗?我喜欢男人的物件,尤其是美观的,你就有这种条件。」
「嗯,够尺寸?还要什幺条件呢?」
「尺寸当然要紧,还有值得重视是体型,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男人很英俊,直到上床之后,发觉他是弯的。」伊丝说。
「弯的可以迁就。」
「不,弯的连我的阴户也几乎弯了,我不喜欢这样的,喜欢直挺挺的,就像你这样。」她笑笑说。
「谢谢你的称讚。」但想到它的丈夫就快出来,胡诚接着又说:
「快把东西放进去,你丈夫出来的话……。」
伊丝却一点儿也不在意。
「又一次我遇到另一男人也很英俊,跟他上床才知道他的前端像窗帘一样,你知道,像『里士』装的窗帘。」伊丝抓住胡诚的大鸡巴又搓又摸说。
「原来你这样挑选,难怪你肯出钱购买。」
「欧洲男人很少实行割礼的,我喜欢前端乾乾净净的,像你这种,最令我满意。」伊丝边说用手搓动他的神经。
他听见浴室中有声音,立即把小腹一缩,把大东西藏在裤内,使他回复原状。
伊丝的丈夫巧好走出浴室。
伊雷向胡诚笑笑,胡诚想可能没有看见刚才的情景,便鬆了一口气。
伊雷跟妻子讲了几句话后,便披着外衣出去,临走还向胡诚挥挥手。
房间内只留伊丝和胡诚。
「你怕我丈夫?」她边笑边躺到床上。
「他怎幺肯把你与一个单身男人留在房内?」
「人生太短,除了快乐,谁担心这一切?过来,我到台湾是来作乐的。」
她伸手向胡诚招着说。
胡诚走过去,伊丝的手便挽在他的颈项上,另一只手已摸向他的腹际。
他感到她的手一抖,就感到下腰一冷,裤子已滑了下来。
「你是惯做扒手的?」
「专扒男人双腿中夹着东西。」
伊丝探到目的物,把它拉到胸前去。
她渐渐地将自己的上衣打开,这时胡诚看见她雪白的胸脯,胸脯前有两点红润的焦点。
她将他搓动着,用她乳沟中的温暖低陷部份向他的私有品搓动。
欧洲女人是狂放的,在伊丝面前,胡诚也很快地嚣张起来。
「脱掉我的衣服。」她吩咐他做。
胡诚将伊丝腰间丝带拉去,衣裙缓缓从它的臀部移下,她白润的腰围,还有腿下金黄色在他的眼前闪耀了。
她把自己的门户张开了。
胡诚向前一动,这时他的鸡巴与它的桃源洞口接触时,像在清泉中淋浴,他向泉水涌入。
「你真热诚,这是我第一次与中国人有肉体关係,哎……你这儿真热。」她半开眼低声说。
他渐渐深入,伊丝充实得有一点站不起来了。
他开始像一个婴孩似地在她的溪水中嬉戏,当钻入与冒出时,他们的神经都收缩起来。
「哎哟!痒……舒服死了……」伊丝浪叫着。
他将双臂紧紧的挤压她,感到她的乳尖在胸前凝固。
「啊……快……用力……小……小穴受不了啦……用力挺……对……那深处最须要……啊……天……上帝呀……快用力呀……嫩穴痒死了……对……对……就这样……啊……达令……你真行……美死了……快快……啊……我太舒服了……啊……那……那是什幺?……,要出来了……达令……我……我不行了……真的……出来了……哎哟……。」
伊丝在一阵浪叫后,双手没命似的紧抱着他,屁股向上狠顶,全身不住颤抖,两眼紧紧的闭着,尽情在享受高潮的乐趣。
在一阵神经收缩后,他播放开来,在她的温泉内,将自己的神经由紧张变为鬆弛,然后将一股精液强劲有力地喷射出来。
他鬆了一口气,很久没有移动。
胡诚躺在伊丝身上,过了很久才倒在她身旁。
胡诚轻轻的退出,看着伊丝娇嫩的身躯,像樱桃似的乳尖仍然凝固着。
她却像个死人似的,苍白的脸色,双眸紧紧的闭着。
过了很久以后,她微微张开眼低声说:
「你把生命的泉源留在我身内,这样真好。」
「为什幺?」胡诚尚在喘息的问。
「我可以拥有一个像你一般的孩子。」
「什幺?」
「你知道做爱的结果怎幺样?会生孩子。」她耸耸肩,毫不在乎地说。
「你疯了?」
「我喜欢中国人的孩子,黑黑的眼睛,黑头髮……」她幻想着又说:
「唔!我要一个含有东方血统的孩子。」
「你丈夫不会介意吗?」
「不!绝对不会介意的,我跟男人在一起做爱,是跟其他女人不同的。」
「怎幺不同?」
「我是从不避孕的。」伊丝回答。
「你疯了!假如你真的有孩子,怎幺办?」
「为什幺这样笨?你看不出来这就是我的目的。」伊丝摇了摇头说。
「目的?……」
「是的!你以为我每到一个地方,找一个男人付钱给他,只为了性享乐?」
「不是为了享乐,是为了什幺?」
「为了孩子!」她停了一会儿才说。
「我不明白,你是有丈夫的,可以拥有与丈夫共生的孩子。」
「你是不明白的,胡诚先生。」
她站起来,走过去点燃一枝烟。
喷出一口烟,缓缓坐回床边。
伊丝伸手抚摸着,低声说:
「我与丈夫虽然结婚,但是一直没有孩子。我应该说……生不出孩子。」她耸耸肩。
「而你们爱孩子,所以你用钱买男人做爱,而他慷慨同意,嗯?」
「不!人是不会这样大方的,其中另有原因。」她淡然一笑说。
「什幺原因?」
「伊雷的父亲是罕有的亿万富翁,已退休了。这个人很固执,立下遗嘱说:「只要儿子生下孩子,他有了孙子,才肯将遗产交给伊雷。」她终于坦白的说出。
点点头,他终于明白了。
「为了遗产,所以一切夫妻关係全不重要了。」
「也不那幺简单,因为我与伊雷都生不出孩子,所以……我们有了协定。」她说。
「什幺协定?」
「他去外面找女人,我去找我的男朋友,这一点大家都平等。」
「伊雷在外面胡搞,如果外面的女人有了孩子,他就有权与我离婚,这是我同意的。」
「你在外面玩男人,条件怎幺样?」
「我在外面玩男人,如果我有了孩子,他就得承认。这个世界男女本来就是平等的,现在你明白了吧!」
「我想我明白了,你这样的勤劳,是希望生出一个儿子来。」
「儿子是次要的,财产才是第一。」
「如果你生下一个中国孩子,你要知道,父亲是我。」
「不,父亲是伊雷。这是我付钱给你的原因,女人对这方面是有利益的,我怀了孕,起码有十个月时间,嗯!十个月中你是找不到我的。」
「你丈夫在外面胡搞,你一点也不生气?」
「不,他在勤劳製造孩子,只要孩子生出来,不管是谁生的,他立刻能继承财产。」
「我全明白了。」
「所以我们要卖力点。」她把手中的香烟丢掉,俯下身,她用唇来吻他的乳头。
她的舌尖移动,从他的乳上移到胸前、腰际与小腹上……。
然后,她张开口,把胡诚的大鸡巴整个含住。
当他渐渐在她的口腔嚣张时,酒店房间的门一开,一个人影闪进来。
「伊雷!」胡诚躺在床上大叫。
伊丝把他放下,回头看了看丈夫。
伊雷明明看清楚床上的一切,但好像一点生气的神态都没有。
他转身,伸手往门外一开,把一个身穿旗袍的中国女人拉了进来。
那个女人胸前的一对乳房正在颤抖,看见胡诚和伊丝脱得光光躺在床上,不禁大惊地张开了口。
伊雷将她拉到房中,在另一张床上坐下,又把那女人拉到他身边。
女人突然不再介意了,嘻嘻一笑,倒在伊雷身边,这时伊雷伸手解开女人的衣扣了,把衣服脱下。
胡诚看着发呆,女人往后一躺,索性张开手脚,让伊雷摆布。
当伊雷把女人的双乳从紧紧的旗袍抖出来,他的另一只手已在解他自己的衣服了。
他一眼瞥见伊雷把裤子脱下后,身上已经是血脉奋张,所有男性的感应全呈现了。
胡诚知道伊雷将要和女人採取行动,便连忙从床上坐起。
「你做什幺?」伊丝一点也不介意,一手拉住他说:
「我们不能在这里。」胡诚说。
「别太古板了,我不介意,你介意什幺吗?」她笑着说。
「他们……。」
「我知道,我丈夫跟那女人做爱,我不在乎,你也用不着。」
「你受得了?」
伊雷已压到女人身上,两团肉球缠在一起,很快地,伊雷已寻到他要找的缝隙了。
「假如把做爱想成是一种工作,你就不会感到害羞和侷促了。」
胡诚睁大眼。
「别忘记,我们是瑞士人,对于性的看法会不同。」伊丝告诉胡诚。
胡诚望了望伊丝,又看看伊雷,整个人楞住。
「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宴会,一共有六十多个人,在一个大厅里,大家一起做爱,每个人都带着妻子或丈夫,到了那儿,各自找寻欢乐──性就是这个样子。」伊丝爽快地对胡诚说。
「性就是这样?」
「是的,不用把这件事看得太紧张。」她回答着,接下又说:
「像一个人需要食物,就张开嘴吃。这儿,也是一样。」她指着阴户说。
「饿了应该吃。而且,除了快乐外,我和伊雷还有更好的理由和目的───一个孩子,一个价值千万的孩子。」
「但是我……我只是一个卖籽种的人。」
「是的!」伊丝回答说:
隔邻那张床上突然发出一阵阵的浪淫声来,还夹杂着沉重的呼吸声来。
胡诚侧头看看,只看见伊雷带回的女人已高翘着双腿呻吟着。
伊雷在女人的腿中进退,完全像一座机器。
借种者!她很不幸,竟也是一个借种者。
胡诚感到好笑,这世界完全变了!
「嘿!你看什幺?我请你到这儿来,是来工作的。」伊丝说。
胡诚倒到伊丝身边去,她拥抱了他。
伊丝的舌尖又在胡诚的身上游动了。上上下下好像要把他完全吞噬掉。
他的大鸡巴又开始耸勤起来。
「快一点,不能让伊雷抢先,我要努力,我要一个小孩。」
「好!给你孩子。」他毅然的说。
事实上在目前的情形下,也只有他才是她真正的主宰者。
胡诚在伊丝的桃源洞口滑行。为了要给她一个孩子,就得涌进去,把自己身体的一切留在她温暖的泉源里。
「快……快……给我一个孩子!我要一个孩子!努力!努力!再努力……。」
在她的浪哼中,尚夹着这种金色的嘶喊。
在四天之内几乎是不眠不休和伊丝做爱,预计所射出的精液足有半杯之多。
伊丝很满意他的服务,额外地赏给了胡诚伍仟元美金。
胡诚送她俩夫妻往机场时,伊丝又公然地和胡诚长吻,然后附在耳边轻声地说:
「这几天正是我的受孕期,你那些强壮的……一定会带给我福气的。」
********************************
一年之后,正当胡诚对这种牛郎生活感到厌倦时,突然接到了一笔由瑞士银行汇来的美金十万元,过了几天又收到一封装着一张婴儿照片的信函。
没有寄信地址,也没有发信人的签名,那张包住婴儿照片的空白信纸,印着一个鲜红的唇印,他会心笑了。
他下决心改头换面,跑到北部来,一方面养尊处优,将自己吃成肥头肥脑地,这是避免再被女人们注意的唯一方法,另一方向也学会了股票操作技术,这是他日后的事业。